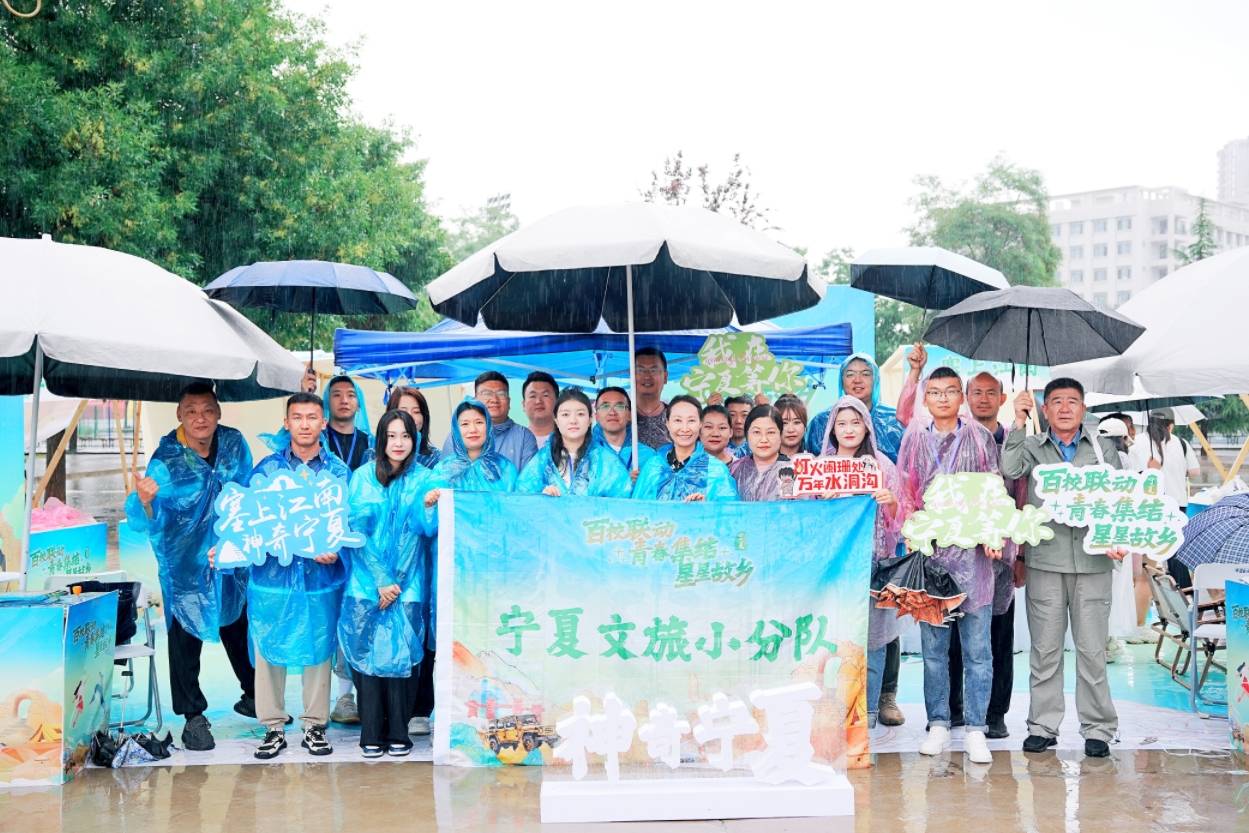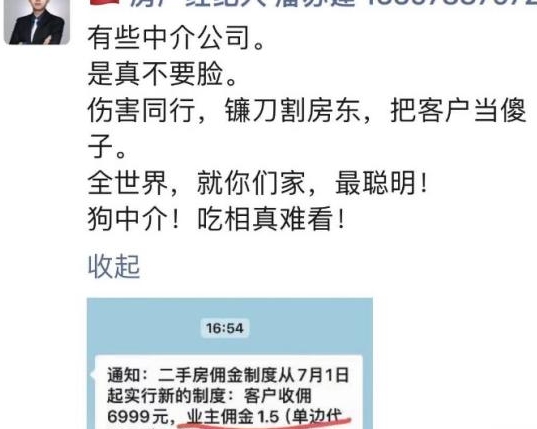过去1年,腾讯集团高层间,新增了一个重要的企业微信群聊。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总裁刘炽平、高级执行副总裁卢山和汤道生等,悉数进入该群。这个群专门针对大模型技术变革,用于分享和讨论最新前沿并跟进业务进展。
很多人说,对大模型,腾讯“不着急”。对此,汤道生表达了不同看法:“着急啊。我们在群里经常讨论,不能说不着急。”
汤道生(Dowson Tong)是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EO,总办成员之一。他1973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早年,他在Oracle和Sendmail公司工作,于2005年回国加入腾讯,从一名系统架构师一路擢升,先后在社交网络事业群和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担任CEO,前者负责QQ业务,后者负责云与to B业务。过去19年,汤道生亲历了腾讯在社交、音乐、to B等关键战场上的关键战役。现在,他是腾讯在AI之战中核心成员之一。
这是中国科技大公司如何思考AI技术革命的一个截面。和我们此前报道的杨植麟、朱啸虎、王小川等创业者、投资人视角不同,汤道生提供了一个大企业经营者的视角看人工智能。
近4小时访谈中,汤道生回答了诸如,“怎么看待价格战”、“在大模型上的投资思考”、“平台型企业和大模型创业公司的关系”等新鲜话题;同时从更长远的视角探讨了在to C和to B两个赛道,腾讯如何看待竞争、业务节奏与组织文化;更重要的是,诞生于上一轮技术革命之中、如今25岁的腾讯,应当怎样应战新一轮技术变革。
在汤道生看来,对于腾讯这样体量的公司,资源上必须确保投入和跟进,做“类OpenAI”的研究与研发;但同时也要保持清醒,“不要把AI等同于大模型,要看得更全面”。
“不是只有做大模型的玩家才是做AI。这就等于认为,只有做手机的企业才在移动时代重要,是很狭隘的。”他说。
你会看到,这位久经互联网战场的业务负责人,罕见地用了这样的表达:“Get a feeling”、“感觉”。他说:“(腾讯)高层对市场和产品的感觉,和使用起来的反馈有紧密关系。”对最新技术,他们会从不同角度获取信息,但最重要的是使用反馈。“我们的感受来自体验,自己用一下市面上的产品,Get a feeling到底这个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问题是在哪?”
以下是对汤道生的访谈。(为方便阅读,作者做了一些文本优化。)
谈平台型企业做AI
“AI不止大模型,keep options open是合理做法”
《潜望》:过去这1年你的状态怎么样?会因为大模型进展太快睡不着觉吗?
汤道生:Emmm,哈哈哈,可能有一点吧。本身我对技术很感兴趣,就算在非常忙的一天会议后,在家里晚上或周末,我会打开一些技术讲解视频看到睡着为止——从另一个角度描述这个状态。
《潜望》:一个经常听到的业界评价是,在大模型浪潮中,腾讯“不着急”,他们说的对吗?腾讯为什么不着急?
汤道生:Pony(马化腾)之前说的是,“不着急拿出半成品”,找对方向、想清楚、保持迭代最重要。到底是起得早重要,还是熬得久更重要?我觉得,不仅仅要起得早,更重要是熬得久——有时候前期过度投入,坚持不下去,反而不能笑到最后。
你看苹果在移动设备上的投入:从最早的Newton(苹果1993年推出的触控掌上电脑),这是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大大的掌上电脑,用手写笔操作;到有Palm那些PDA(也是一款手写掌上电脑);下一阶段是iPod音乐播放器;再到iPhone。哪怕苹果,也是超过10年不同产品形态的迭代,才抓到移动设备机会——所以重要的不是谁最早做PDA,而是谁最后占领市场。
《潜望》:对大模型,腾讯FOMO(怕错过)过吗?
汤道生:当然会怕错失机会,企业时刻都需要有危机感。腾讯这个体量的企业,对每次技术变革或范式变化,都必须严阵以待,确保资源投入。
但大模型只是AI大赛道中的一部分,人工智能领域的很多其他技术路线也很值得关注,要搭建一套有用的智能系统,大模型也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模块。
不是只有做大模型的玩家才是做AI。这就等于认为,只有做手机的企业才在移动时代重要,是很狭隘的。起码我尽量让团队看得更全面一些。
腾讯的机制还是比较有生命力,各自团队都在关注AI跟自己业务有什么关系,有多点布局。所以,怕错过是正常的,尤其对于我们,keep options open(保留选择的空间)是合理做法。
《潜望》:腾讯CSIG(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在AI上的布局总体是怎样的?
汤道生:我们的AI布局大致分四层:基础设施、模型管理工具与引擎框架、大模型与模型商店、应用场景。
底层是基础设施,包括打造高性能的计算,用高速网络把集群连起来,配上高性能、高性价比存储,让训练更快,这是云业务基础。
往上走是工具层,做大模型训练,需要一套工具链,包括标签管理、推理加速等,也有搭建一套RAG(检索增强生成)系统的引擎框架,这也是我们会提供的能力。
然后是大家关注的模型层。公司重点研发的是混元大模型,已经支持了内部600多个应用。我们也和混元团队紧密合作,开拓更多调用大模型的产业场景,满足客户生图文、生图、生视频、生3D的需求。不同客户场景,对模型也有不同需求。除了混元外,腾讯云也支持客户选择其他模型,有些客户也会用我们的模型工具来精调其他开源模型如百川、GLM等。
再往上是应用层,腾讯本来就有很多to C与to B产品,每个产品都有服务用户的场景,他们都会思考怎么用AI来提升用户体验、提高使用效率。比如在CSIG的企业应用中,腾讯会议就用大模型来生成会议纪要,腾讯乐享就用大模型构建熟悉企业文档库的智能助手,Coding研发平台用大模型来生成代码。
《潜望》:关于AI,你目前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汤道生:除了通用大模型以外,我比较看重怎么能让大家在产业场景把AI用起来,需要提供什么工具和能力。目前我感觉,可能还是很大程度回到RAG(检索增强生成)的模式,降低出现幻觉的概率。
同时我也比较重视,怎么把握住“智能体”的方向。如何组合不同技术模块,搭建更有价值的应用,解决具体问题,建立合理的商业模式。
此外,上一个阶段的AI企业,很多都没有做出标准产品,做不到同类场景的快速复制,只能靠堆人力来不断做项目,做个性化交付,这就很难建立规模化的商业模式,也导致常年亏损没法盈利。新一代的AI企业要引以为鉴,还是要通过相对标准的产品去建立业务模式,减少个性化交付。
《潜望》:怎么看“模型即产品”、“模型即应用”这类说法?
汤道生:我不是很在意一些概念化的包装。产品就是产品,模型本身不是完整产品,要搭很多能力。用户要用得爽,不是简单的“模型吐东西”。
《潜望》:近期业界很关注的一条新闻是,国内大模型大降价。从字节开始,阿里、百度、腾讯跟进。腾讯跟进决策是怎么做的?
汤道生:实际行业的降价,没有想象那么大。(很多公司的动作是)输入的token(input token)免费,输出的token(output token)没太大影响。我一开始比较反对价格战,但是全行业都在这么做,我们也要有所行动。国内企业太喜欢用价格战来竞争,经常用亏损来换取市场份额,而不是赢在能力、赢在效果。
在资本充裕的状况下,有的公司爱用补贴的打法来抢市场,但腾讯比较重视可持续发展。我看损益表(P&L)看得很紧,每个业务都应该算清楚成本,合理定价,避免靠别人的利润补贴自己的亏损。我做任何业务都会想:合理的商业模式该怎样?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投入和产出才能长期健康发展?
云也一样。早期大家都只在意市场规模与份额,我们也曾经跟着用亏损来换市场、拿项目,后来发现这些亏损并没带来客户的认可与忠诚,甚至有很多管理动作变形。所以,现在坚持可持续发展,聚焦产品,夯实技术,管好价格,持续优化成本,让每个产品与销售单元最终都能养活自己。
有时候,大环境没这么好,反而对我们的做法更有利。你不需要去更多被资本市场的浮躁牵引,回到业务本质。业务的根本,本来就该看看你的成本多少,你赚多少,你的利润能养多大团队,才可以健康可持续发展——如果你认真看业务与财务数据,看看清楚每项投入与产出,你就看得到真相。
总的来说,我们是细水长流,看准了会坚持,不是很浪的那种。
谈平台型企业和大模型创业公司的关系
“谁有机会打造出新一代的C端用户入口?”
《潜望》:从全球看,大模型创业公司到今天都还依赖平台型公司。现阶段,他们对平台型企业有哪些具体诉求?
汤道生:对于创业公司,第一要能持续拿到投资,做大模型挺烧钱的。
第二是要算力。算力早期非常紧缺,谁能供给,它就愿意和谁合作;当供给慢慢充裕,企业也会开始挑,哪些平台提供的资源效率更高——市场没有卡的时候,哪里有都会要;现在可能会放掉零散资源,尽量把资源集中起来,算清楚ROI(投资回报率)。大家拿裸资源成本差异不会很大,但不同云企业、平台厂商的积累不同,在训练效率、服务能力、定价上都可能有差异。
第三是技术。你如果跑一个大集群做训练,非常依赖底层云平台技术的支持,比如万一有台GPU服务器宕机了,如何从checkpoint(检查点)快速恢复训练,不用从0开始,还要看GPU卡互联的网络带宽与速度,和模型存储的性能与成本。所以我们的星脉网络与GooseFS都挺受欢迎。
我看好几家(大模型公司)都在使用多个云厂商资源。有的厂商资源用在训练,有的用在推理,有的针对训练前的各种数据处理工作。
《潜望》:在投资策略和云计算战略上,有些平台型企业更激进。例如,他们会地毯式投资大模型初创公司,并用算力置换投资额。你怎么看这种做法?
汤道生:如果投资的企业成功了,需要持续的云消耗,这当然最好了,对云业务是极好的收入来源。不过,当前训练大模型的GPU资源很紧张,也得有足够多的GPU卡用来投资才行。
不管是用云资源还是用资金来投资,实际上还是要花钱的。这么多玩家,到底能挑中多少赢家?这是考验你的投资者眼光,不是考验你的基础设施能力。
去年有GPU算力荒,大模型企业拿到钱也要去买GPU。如果投资过程中,在现金之外打包算力,确保算力供给,创业者也无所谓。于是出现了一些公司“用资源来投资”的交换现象。
但在算力供给充裕、市场高效运作的状态,真正有前景的企业与他们原来的投资者,肯定还是想要现金。这能确保他们的资源投向更灵活,挑选云厂商也可以看性价比,看谁的技术、服务更好,这是最高效的市场行为。之前因为(算力)供给侧出现了问题,所以才会出现“捆绑”的现象。
《潜望》:以大模型来刺激云收入,是长期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吗?
汤道生:新科技早期在风口,大量资本驱动创业公司野蛮生长,可能会过度投资,好多玩家也许是泡沫的一部分。如果云的收入太依赖资本驱动的创业公司来消耗,一旦泡沫爆了,一些客户会消失,业绩会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会比较痛苦。
你看九十年代,互联网创业公司百花齐放,我当年在Oracle,公司赚了很多互联网公司买数据库的钱;但后来,90%的互联网企业到2000年没了,导致2000年代初期业绩压力很大。
《潜望》:今天,大模型产业的状态是?
汤道生:很早期。大家都在跑马圈地,尝试着不同的商业模式。有的在追Scaling Law(规模效应),有的在打造to C市场新入口,有的在做产业落地,非常热闹。
《潜望》:所以,“捆绑云做投资”是一个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特殊现象?
汤道生:对。还有一点,你如果投大模型企业,你投的可能是——随便说——给它投5亿美金吧。假设它1年消耗3亿算力,假设是0毛利与成本分5年摊销,对于云厂商的资本支出可能是5倍。虽然你是用3亿算力投资了它1年的消耗,但你实际现金是花了15亿出来,用来买GPU。
我不了解友商在每家投资的细节,不知道是用云代金券,还是锁定某些GPU卡资源;但5年的不确定性很大,也许GPU技术升级,原来投资的GPU卡大大贬值;也许被投企业发展不理想,后续用不了所有云代金券,可能要想办法换回现金。
这里有很多复杂问题,经营起来有特别多账要算。
《潜望》:在你看来,基础大模型,到底是巨头还是创业公司的机会?
汤道生:基础大模型,在国内,大厂的资源多一些,在AI方面或多或少已经投了很长时间;但创业公司动作更灵活,在吸引年轻人才方面,也有他们的优势。
一旦进入模型应用领域,创业公司最好与大厂做差异化竞争,进入大厂不太关心的市场,或者大厂原来不熟悉的业务模式,比如像滴滴当年做打车。
像月之暗面、百川、MiniMax等这样的创业公司,都有机会跳出来赢得市场。除了因为他们的大模型技术水平好,他们也很关注在C端应用与B端垂直赛道的投入。
比如,大家都在尝试用chatbot app来满足用户的搜索需求——谁有机会抢到更多搜索的市场份额?或者打造出一个新一代的C端用户入口?
谈腾讯的快慢与业务风格
“有很多对的事,短期看上去也许都很蠢”
《潜望》:腾讯5月30日发布C端产品元宝,为什么在这个时点才发布?
汤道生:产品要准备好。如果自己觉得准备还不充分,等一等问题不大。不是什么都唯快不破。
我们要先把技术掌握透,确保用户体验好,而且市场也没到“生死时速”、“争分夺秒”的地步。随着市场慢慢成型,用户需求更明确、清晰,我们也会加快步伐。过去半年,已经有明显的变化,新产品、新版本发布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从技术长期布局投入,转到产品的市场去进攻。
《潜望》:有人问,在大模型上,腾讯慢了吗?
汤道生:其实也还好,起码我不觉得。
不过,就算慢又怎么样?你可以说,Google你慢了,你们没有1995年就做搜索引擎,那个时候AltaVista多牛。(注:AltaVista创立于1995年,是互联网早期最知名的搜索引擎公司之一,谷歌成立于1998年。)但是who cares?他们现在才是赢家,技术也是非常领先的。
《潜望》:外界对腾讯做业务的风格有一个评价是,“跟着、跟着,慢慢就领先了”,你怎么看?
汤道生:业界往往低估了腾讯长跑做产品的能力。如果你要赢,难道只是跟着就能赢吗?(笑)
实际上我们做事风格是,持续打磨产品,不断改善体验,只要赢得用户口碑就有机会领先。一些自媒体总喜欢把腾讯与“跟随”关联上。我们不仅是“跟着、跟着”,如果没有创新与亮点,不可能最终成为market leader(市场领先者)。
《潜望》:“后发制人”这个描述准确吗?后发制人的诀窍是什么?
汤道生:历史上腾讯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业务有很多,有的取得胜利,有的徒劳无功。在取得胜利的业务中,有的在市场早期就已经参与,有的较晚才投入,能否“制人”还是取决于后续的执行。一旦决定要长期投入某个赛道,更重要是能否找到差异化打法,对产品体验的持续改进,而不是“先发”还是“后发”。
比如,智能手机的普及。iPhone绝对是智能手机市场上最重要的推手,但苹果是第一家做智能手机吗?其实并不是。起码当年多普达就比iPhone要更早嘛。“后发制人”的诀窍在于,你有没有满足用户痛点,提供更好的体验,并且持续做投入。
另外,坚持也很重要,有时候甚至要能耐心地等待对手决策失误。有些企业喜欢在新赛道上一开始就高举高打,投入大,亏损多,粗放的经营让你找不到关键路径。因为长期巨额亏损,结果坚持不下去。
QQ音乐我个人有过一些经历。早年,有很多平台在竞争,争夺PC时代的在线音乐市场。QQ音乐也面临很大挑战——内容版权费逐年增加、盗版严重、没有商业模式等一系列问题。但我们坚持做正版音乐,获得版权方的长期信任,不断完善曲库,持续打击盗版,避免性价比低的版权采买,尽量控制亏损。平台间不理性竞争,导致长期巨额亏损。到移动时代,很多人熬不住了。
幸好我们就坚持下来。从2005年到2018年TME(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上市,经历了很多人竞争到很多人放弃,再到商业规则终于健康建立的过程。
《潜望》:它的转折点在哪?以及,时间节奏应该怎样?
汤道生:转折点在于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给予平台去打击盗版的支持。当然我们要有技术手段,通过全网扫描与监测,及时发现哪里有盗版,把握最重要的时间窗口,让盗版音乐撤下。如果不在最关键时间控制盗版传播,就很难吸引用户去到有正版的音乐平台上。
时间节奏不好说,其实就是等待——等待打乱规则、乱出牌的对手放弃市场,你就可以打造健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打击盗版长期肯定对的,是整个创作生态的根基。但也是苦功夫,不是短期见效,得长期坚持;而且平台打击盗版,你的竞争对手短期可能会受益,但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做了。
有很多对的事,短期看上去也许都很蠢。
《潜望》:总体而言,应该怎么总结腾讯的做事风格?可以举一个例子表达这种风格吗?
汤道生:不同团队的做事风格可能不太一样,大部分产品团队的风格应该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更讲究产品体验,迭代,先小范围满足用户需求,验证后大家认同了,有口碑传播再加大投入——这比较符合腾讯。
拿会议来说吧。早期我想做腾讯会议,但国内市场还没有这个品类,需求并不明确。我不可能拍胸口跟公司说:请相信我!如果能给我2000人(当时Zoom在国内大概有这么多研发人员),我们能做一个很有价值的视频会议软件——虽然QQ和微信都已经占领了主要的音视频通讯市场。但谁会相信你?
我们解题方法是:好吧,(在线会议)这好像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细分市场,QQ与微信也没有特别服务好开会的场景,凭着原来QQ团队在音视频技术的积累,先投入几十人的小团队去研发,搞个内部版本给小范围使用,不断迭代,磨产品,看到有用户反馈觉得好,再去申请加大投入——我们是靠用户的使用,来验证有没有找对方向。
《潜望》:腾讯会议开始算一个边缘项目?从领导者角度你怎么发现、识别有潜力的边缘项目,扶植它长大?你怎么知道自己没有遏制它?
汤道生:这是我想做的,我怎么会遏制它呢?(笑)
很多边缘项目其实挺不容易的。既然是边缘,公司就不会分配重点资源支持了,而且投入初期肯定都是亏损的,需要其他业务收入补贴来养。然后就等待时机,希望能一步步做大。大家的年终奖金跟业务收入利润又强关联,怎么持续鼓励、留住团队,让他们看到这类内部创业项目的长期价值与发展机会?这很考验项目负责人的能力。
如果追溯起来,早年我想做企业会议场景,是因为我觉得拨号电话会议不够便利。此外,很多会议产品,没有离开软硬一体专属垂直整合的模式,软件相互不兼容,硬件价格都很高。以前WebEx加Cisco大屏设备,好像要10万块一台。只有大公司的董事局会议室,才愿意投这么多钱在会议系统,不可能普及到更多场景。
其实,科技大的发展趋势不停在重复———从软硬一体专属垂直整合的产品,到软硬件分开、横向软件平台打通多家硬件的生态模式。比如Linux出现之前,很多Unix服务器公司如Sun Microsystems、HP、IBM,都是自己的操作系统与硬件强绑定,芯片也专属,可以溢价。后来免费操作平台像Linux出现,兼容各类基于x86芯片的服务器,相对廉价的x86服务器市场如雨后春笋,横扫了垂直整合的传统Unix服务器玩家。因此,经营网站的成本大大降低,互联网也加速普及起来。原来靠卖硬件、配专属软件的模式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市场、高效率的技术产业生态。这在工作站、服务器市场出现过,我们相信会议系统也一样。
所以,我让Lori(吴祖榕,腾讯会议负责人)牵头做会议。他一开始说,哎呀,Zoom在国内就有2000多人,你给我30人,怎么搞啊?但小团队挑了一些最核心的功能,搞了搞了就有个基础产品原型出来,然后内部试用,不断迭代打磨体验。
《潜望》: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应用出现爆发性增长的拐点?
汤道生:我们的产品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19年12月底上线,2020年春节是最关键的时间窗,大家要复课、复工。其他公司后来也发现了这个机会,开始重兵投入去追。但我们在疫情前已经做了1年半,所以产品的体验与稳定性会好很多。
在通讯类市场,网络效应特别强,相对更分秒必争,你必须抓住时间窗。一旦把用户网络建起来,别人想再推另一个App打进你的网络就会难很多。
《潜望》:怎么激励团队,快速应对稍纵即逝的时间窗?
汤道生:因为有前期的产品铺垫,用户马上能用起来,就抓住了关键时间窗。疫情一开始,各类需求扑面而来,总办成员们都在帮大家克服各种困难,也动用了微信群视频界面加大推广腾讯会议。
我记得,初八前已经跟Pony、Martin有晨会讨论,他们亲自调动资源,马上批了很多人力,CSIG(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其他产品的研发人员被临时借用,TEG(技术工程事业群)也积极帮我们搭设备、扩容——这个团队从上线前几十人,到关键时期的百人、百人去加。一方面是承担着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产品的发展。
我们在看到明确机遇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加大投入,协同作战可以很敏捷的。
《潜望》:在看到确定性机会时的敏捷投入,投入能有多大?
汤道生:看项目情况与实际需求吧。腾讯会议在疫情期间免费供大家使用,光带宽成本就一年十亿元以上,各类资源的投入都很多。AI与大模型的投入就更大了,拉通了公司多个BG,不同团队负责不同板块,调动了很多技术专家,而且计算资源投入也非常巨大,还有对外投资呢。所以要看具体context(注:赛道与战场)了。
《潜望》:在这种做事风格之下,腾讯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创新应该更“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汤道生:这个问题不能用选择题方式来回答。我以前认知是“自下而上”,但后来越想越觉得,上或下是相对的。很多时候,创新是双向进行。在CSIG,我会挑市场与赛道,选择在哪投入。启动后,需要业务负责人带领团队不断探索,过程中团队也给予很多反馈,不断讨论、不断优化策略。
以腾讯会议为例,虽然我先提出来要做这个产品,但会议功能的持续迭代,以及产品战略与商业化细节,比如纯做软件服务、兼容多家硬件设备的想法,好多是Lori与团队提的。
在创新的过程中,每个人角色不一样,都很重要。没有高层认同,创新的资源可能有限(当然有时候太多资源,也未必是好事),没有团队的智慧与贡献,不断解决执行中现实的问题,创新也难以持续稳定地涌现和落地。
《潜望》:为什么中国to C产品(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发展很繁荣,to B软件却难以长出千亿美金的公司?
汤道生:的确,在国内,要不做专属硬件,只做兼容多硬件、横向整合的通用软件服务很挑战、很难坚持。虽然腾讯会议在国内已经是市场领导者,但到今天仍然亏损。
国内软件服务行业发展其实有点畸形,太过于重硬轻软,对比全球所倡导的“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软件正在吞噬世界)、“Software Defined this and that”(软件定义一切)有明显差异。在国内很多项目招标,客户经常只预留很小比例给软件产品,大部分预算都放在硬件上。一些厂商们往往以硬件利润来补贴软件,用垂直整合来占领市场,因此国内软件企业利润空间极小,很难培养出像微软、Oracle、SAP这样规模的软件企业,产业规模也与全球软件市场差距不断拉大。
在全球市场,芯片、硬件与软件厂商分别有主导玩家,产业生态蓬勃,各行业有自己的市场与利润空间,多元竞争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应该是国内科技产业发展的长期努力方向。
《潜望》:说回大模型,外界感受到腾讯“不着急”,是因为没看到确定性的机会?
汤道生:外部感受不着急,也许是因为大家看到一些企业创始人,也开始做KOL,不断向市场发出很强信号。当然这是很好的产品推广,既获得行业关注,也能获得投资。但我们不擅长这样,我们低调,也许就是我们的短板。
但我们并不是不着急,只不过很少刻意对外讲All in的口号。一个长周期的业务,前期资源投得越猛,坚持的难度与压力就越大,穿越周期的韧性、耐性就会更少。我们在AI投入是长期的,既然目标很清楚了,那就有节奏地跑。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腾讯的高层来说,我们会持续从不同角度了解行业情况,通过使用产品,不断地验证想法,试错和迭代产品。好多时候,我们的感受都来自自身的体验,自己用一下市面上的产品,真实地感受一下(Get a feeling),到底这个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问题在哪?
过去腾讯一直都是这么做产品的。我们对市场与产品的判断,往往基于用起来的感受。所以我们做C端产品时会比较顺,因为大家都可以使用,你马上知道做得好不好,别人很难忽悠你。通过去使用、去感受、去体验,得到一些牵引团队的方向和方法。
游戏就很典型,我们在关键战场,比如当年的PUBG、《王者》,在关键时刻都是全员一起玩,每天玩。
谈组织变革与个体发展
“我有一个‘721’方法”
《潜望》:腾讯“930变革”后,你从管理社交网络事业群(SNG),转为负责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在一家to C文化浓郁的公司做to B,有摸索出好方法吗?
汤道生:肯定无法套用腾讯过去to C业务的成功方式,但也必须从原来积累多年的技术优势与平台资源找切入点,打造腾讯独特的to B打法。
比如,我们发挥微信生态的优势,利用线下的微信扫码,连接小程序与企业微信,打造营、销、服一体化的CRM体系,受到很多C端企业的认可;又比如腾讯的内容优势,也是早期CSIG服务车企的重要切入点。一旦有了切入点,我们就能逐步扩展到更多云产品的合作机会。
To B业务很复杂,每个客户、每个项目都需要多个角色协同,需要分工清晰,有完善流程与系统支持。我们要聚焦自研产品,保证考核规则与目标保持一致,让合作伙伴围绕我们的产品提供服务,培养广泛的生态伙伴——这都是我们不断踩坑、不断填坑后,逐步探索出来的方法。
《潜望》:CSIG成立这几年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以2022年为分界点你做了一系列大手笔调整。
汤道生:第一阶段是粗放发展阶段。CSIG成立以后,我们成立了很多行业团队,各自整合内外部资源,打造行业解决方案,找了很多合作伙伴,也引进了一些集成商。当时在收入上定下一个目标,然后野蛮生长,没有管得很细。
虽然公有云发展迅速,为了赢得大客户有不少产品低价、甚至亏着来卖,供应链管理也比较粗放,资源利用率低,成本高,所以毛利率很低,亏损严重。私有云方面,很多销售借着大集成拿了不少区域项目的大单,媒体上与友商比拼谁在哪个省市拿的单更大,但因为包了好多东西,找了很多伙伴来交付,后来很多集成项目都没交付好——到今天还在处理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
这个阶段,很多团队都能把收入做得虚高,虽然也完成了收入目标,但转售别人的东西不会给自己产品带来积累——销售会解释,反正计收规则允许转售嘛。甚至后来,有些伙伴把精力放在了专攻我们的销售上,让销售拿到的单全总包给他们。
接着到第二个阶段,我们收紧了计收规则,比如转售与短信不能全额计收了。自研产品得到更多市场验证的机会,比如云底座TCE、音视频通讯TRTC、数据库TDSQL等产品都赢得更大市场份额,公有云上的大数据、AI与SaaS产品也迎来高速增长。同时,产品管理与销售管理变得更规范,项目管理与交付生态更完善。到今天差不多3年了,规则与流程越来越清晰,目标也越来越聚焦。
《潜望》:做这个变革前酝酿了多长时间?
汤道生:蛮久的。早年我苦口婆心跟销售说:哎呀,还是卖自己的产品才有意义,别去盲目追大单回来,一堆我们交付不了的事。但你讲了都没用。虽然大家口头上说:Yes,sir!我理解,我已经在这么推了!——但最后,大家的行为都是被销售规则、考核规则牵引。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调规则。
调规则有很多反弹。很多人说,这样不够to B。很多人怀疑你,收入会降低。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需要做的决定,你还是要做。所以,我们就下决心挤压不健康收入。
经过两年多的调整后,一系列管理手段慢慢体现出效果,大家在做更健康的事。
《潜望》:调整的最重要几个规则能不能列举一下?
汤道生:例如,转售只计收毛利,包括第三方硬件与短信也只计收毛利。转售的外部白名单与精选产品基本砍掉了90%以上。
再比如交付服务不算自研收入,让产品团队不去贪消耗人力的交付与定开收入,这样就可以大力推动由伙伴来提供交付与定开服务,以此作为他们的商业模式,让他们更愿意推广与推荐我们自研产品。这也逼着我们加强产品的易用性、生态伙伴的培训、认证体系等。
《潜望》:争夺国内第一名还会是腾讯云的目标吗?
汤道生:我不太在意我们在整体云市场的份额排名。我和一些研究机构负责人也说过,很多排名的记分项都不是很严谨,经常用苹果来跟橘子来对比,很多厂商提供的数据都有比较多水分。例如,云厂商大多仍然把短信收入作为云业务收入构成,大家还有很多集成类项目收入放在“云”的概念下包装。
现在我更关心我们产品在每个细分赛道的市场份额与渗透率,比如音视频服务我们是不是第一?数据库我是在什么位置?大数据领域,市场份额有没有往上走?等等。
《潜望》:Dowson,你已经是中国顶级的职业经理人了,你还有苦恼吗?
汤道生:苦恼总会有啊。人生有很多事是不如意或不可控的。(笑)
《潜望》:我记得1998-1999年,你在美国创过业,那时互联网快要bubble burst(泡沫破裂)了。
汤道生:在那段时间我刚离开了Oracle,曾经做过一个多来源信息(crowd sourcing,注:众包)的、软件相关的知识问答网站。知识问答很难向用户收费,互联网上有太多免费信息,也有很多热心人在社区论坛贡献经验,后来判断这个模式做不起来,就放弃了。
接着我就进入了一个做企业级邮件服务的创业公司:Sendmail。不久后,互联网泡沫破裂。这家公司现金短缺而且持续亏损,需要收缩团队来降成本。在这个降本增效过程中,我是幸存者——本来有4个研发经理,最后留1个,公司选了我。这个过程中,学会了要聚焦最重要的事,挑选精干部队来提高效能,鼓励团队保持积极心态,面向长远目标。
《潜望》:你32岁进入腾讯时是什么心态?有面试吗?
汤道生:当年我五一假期从美国来深圳面试,走进大堂,从坐电梯到办公室,一路黑黑的不开灯,感觉不太像正经的办公地方。在美国,假期时办公大堂与电梯口也是不会熄灯的。当时就有些担心这家公司状况。(笑)我摸黑走到Tony(腾讯创始人之一、原CTO张志东)办公室,跟他聊。
当时腾讯并不是很大的企业。打动我的是,我在美国一直做企业软件服务,但这里可以加入可能性更多的互联网行业。说实话,当时也没看到美国任何一家即时通讯公司能独立上市,即时通讯在全球市场是相对边缘的小业务,AIM、Yahoo! Messenger都是免费而亏钱的服务,没有商业模式。一开始对腾讯的发展前景还有蛮多问号的。
但后来越来越理解腾讯的业务模式与优势,在公司内也找到很多学习与成长的机会,结果就在腾讯待到现在。
《潜望》:在你看来,什么是一名卓越的领导者?
汤道生:太多不同风格的领导都能成功,我认为卓越领导者没有一个固定画像。我只能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尽量比别人看远一点、多想一步,才能带领团队往正确的方向前行。
在业务管理中的资源分配需要有节奏,我有一个“721”方法。70%的资源是投入短期最重要的核心业务,投入足够的精力确保成功;20%是投入在发展中的新产品、新机会,这种机会相对清晰,可能再多两年,就会进入商业化变现,可以补充成熟业务的增长逐步放缓;最后的10%是投在仍处于发展早期的前沿技术,面向未来机会布局,可能要三五年甚至更久才能带来商业回报。
在7和2的部分一般会有很多种的实现路线,最强、最有经验的部队往往都投入在这里;但卓越的管理者需要有判断力,也要能在1的部分敢于下赌注,承担未知的风险。
《潜望》:“好领导”和“好人”是相互排斥的吗?
汤道生:不能叫排斥,但有些地方你要取舍。大家不仅仅希望每天过来工作很开心,优秀人才都有职业发展诉求,希望在一个能赢的团队里做一番事。好领导的一个基本条件:你要能把事做成啊。如果你做不成的话,就肯定不算。
你要做成事,就要做对的决策。遇到一些能力不足的成员,不能为团队达成目标作出贡献,就需要换掉。站在被替换者的角度来看,你是坏人。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来看,“啊,终于把不行的人换掉了”。对他们来讲,你既是好领导,也是好人。
《潜望》:你成长过程中,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
汤道生:《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Be proactive(主动)。(注:90年代的版本这么叫,后来版本改成take initiative。)
主动,不是指你做事主动这么简单。主动,是你的思维要掌控自己的情绪——别人不能让你不高兴,只有你可以让自己不高兴;不管环境怎么伤害你,你仍然可以不受伤害。这对我做事遇到困难,或者人生遇到挫折,很快拿回正能量,有很大帮助。
《潜望》:你的业余时间会做什么?
汤道生:现在主要看视频,看各种各样的内容。我喜欢像海绵一样吸收新东西。但我看的东西很杂,什么都看。看最多的应该是科普类的内容,比如有关半导体产业的、生命科学的、神经网络的等等。
我也挺喜欢看采访类内容,比如Lex Fridman的podcast。之前还碰到一位印度博主,采访印度不同领域的人,有政商的、投资的人,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比如有一段谈到印度的人才外流,那印度精英觉得印度人才流到美国是扩大印度裔的全球影响力,并不是坏事,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挺有启发的。
有空时我也喜欢看电影、看电视剧,放松一下。最近刚看完《庆余年2》,1.5倍速。(笑)
《潜望》:Jim Collins在《从优秀到卓越》有一个观点:技术应该作为加速器而非驱动器来使用,优秀公司从不把技术作为引发变革的主要手段,然而,他们在应用精心选择的技术方面却是先驱。
汤道生:是也不是。有些企业就是靠一个新技术搭建整个体系。比如,你说是因为GPU所以有英伟达?还是因为有英伟达才有GPU?很难讲清楚。
但我们学工程的认为,技术是手段、是工具,核心是看你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搞清楚问题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去找工具。一个人对技术的理解越广,解题工具箱的工具越多,你就更能把它组装起来。这个过程还要理解好每个工具的边界,什么可以做到、什么不可能做到,一步步把不同能力组合起来。
《潜望》:最后问一个宏大一点的问题,像腾讯这样诞生于上一代技术变革之中,已经20多年历史的公司,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下一轮的技术变革?
汤道生:保持开放、保持好奇。就像刚才讲的资源分配的“721法则”一样,一般丢掉一些大机会,很多时候是对远期变革,也就是“1”的部分,没关注到,或者投入不够、好奇心不够。
面对不确定,有些人不喜欢或不愿意,但你永远应该对它保持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