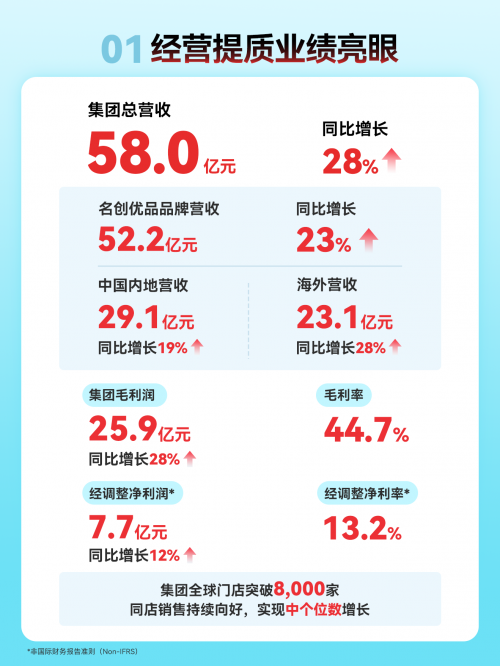林澜
在一次省级学术研讨会上,张振宇医生在台上回答了一个关于颅颈交界区肿瘤手术的问题。他语速不快,手势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他先是分析了影像学上的难点,再指出手术入路选择中的关键风险点,最后提出“以最小损伤换取最大恢复”的理念,赢得了会场里不少同行的点头。那一刻,我决定将这次专访的开端放在这里。
面对我的问题,他笑了笑,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但从他的履历中,很难找到“普通”的痕迹。自2014年10月,他一直担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神经外科的副顾问医生,十年的临床积累让他几乎见证了中国神经外科在复杂手术领域的发展轨迹。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广东省医师协会神经修复专业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以及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这些职务让他不仅是手术室里的执行者,更是行业规范与学术讨论中的重要声音。
“有些病人,你不能只看手术当天的成功率,还要看他们五年后的生活质量。”他强调。这句话并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他在一次脊髓肿瘤手术后的真实体会。那名患者术前已经长期卧床,术后在康复期逐渐能够重新站立。张振宇在复盘时写下详细的记录,并在团队会议上分享改进建议,这一案例后来被作为医院内部的教学材料使用。
谈到自己在委员会中的工作,他并不急于强调职务,而是用实例说明价值。在广东省医师协会神经修复专业医师分会,他与来自不同医院的医生们共同探讨如何统一神经修复治疗的路径。他回忆道,有些同仁认为应更注重早期干预,而另一些则坚持循序渐进。张振宇常常拿出自己手术后的长期随访数据,让讨论落在具体的病程之上。“当大家看见实实在在的康复曲线时,争议才会逐渐缩小。”
行业的变化在他眼里并不抽象。人口老龄化、慢性神经疾病增多、医生人力紧张,这些趋势构成了现实的压力。张振宇说:“如果不能形成跨学科的整体解决方案,单靠外科手术是不够的。”他特别提到在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如何把外科治疗与中西医结合疗法进行对话。他不认为这是简单的“拼接”,而是一种动态的配合,需要在真实病例中找到平衡点。这种态度使得他在多次讨论中成为协调者。
值得注意的是,张振宇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单一的专业框架里。他强调医生需要有跨界的思维。他提到自己与神经电生理团队合作时,常常在手术设计中引入电生理数据,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神经损伤。“这就像走夜路,手电筒能让你看见更多,但方向还是你来决定。”他用这样的比喻来解释复杂的手术逻辑。
我问他,十年的坚持是否会让人感到疲惫。他摇摇头,讲起了那些病人送来的锦旗和信件。在他看来,那些印着感激之词的布面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患者家属最真切的心声。他记得一位小儿脑瘫患儿的母亲,在孩子康复过程中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医生,我们全家都因为你重新燃起了希望。”他说,那一刻,疲惫就不再重要。
然而,他也清醒地看到行业的局限。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医生培训的瓶颈、临床与科研脱节的问题,都是需要面对的挑战。他认为自己在岗位上的意义,不仅是完成一台又一台手术,还要把经验转化为可以被更多同行学习的标准与方法。“只有这样,行业才会真正进步,而不是停留在个别人的突破上。”
张振宇的思考中,总能听到一种“整体观”的声音。无论是对个体患者的长远康复,还是对行业标准的统一探索,他的逻辑都是在不断寻找联系与平衡。这种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不同的学术组织中,总能发挥超越头衔本身的影响力。
当专访接近尾声时,他没有给出激昂的宣言,而是平静地说:“外科医生面对的不只是病灶,而是一个完整的人生。”这句话让我在整理采访稿时反复回味。它不仅是他对医学的理解,更是他对行业的责任感写照。